从2023年6月事件发生到2025年3月,成都地铁偷拍诬陷案的二审竟然经历了六次调解,每次耗时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,最终却以“涉事女生未亲自出席”“双方分歧仍存”草草收场。这种马拉松式的调解程序,表面上打着“化解矛盾”的旗号,实则是司法体系对个体权益的傲慢敷衍。官方宣称“分歧已缩小”,但仔细看看调解内容就会发现,核心矛盾始终在原地打转——何先生坚持公开道歉和赔偿的诉求,而涉事女生连面都不露,仅通过律师抛出“私下道歉”或“匿名声明”等敷衍方案。这种“调解”根本就是一场单方面的精神消耗战:何先生要请假、跑法院、反复陈述诉求,而被告方却连露脸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。官方所谓的“调解诚意”,不过是让受害者用时间和精力为诬告者的过错买单。
更荒诞的是,法院对公开道歉的“法律意义”解读充满双标。根据《民法典》,公开道歉是恢复名誉的必要手段,但一审判决却以“被告已私下道歉”“公开道歉可能激化矛盾”为由驳回诉求。这种逻辑简直荒谬——如果私下道歉有用,何先生何必起诉?诬陷行为发生在地铁这样的公共场所,对名誉的损害本就是公开的,凭什么要求受害者接受私下的、敷衍的道歉?法院用“维护社会和谐”的幌子袒护被告,本质上是在纵容诬告者逃避责任,让“社死”受害者的冤屈永远无法昭雪。
最讽刺的是,这场调解闹剧暴露了司法系统对“弱者”的伪善。何先生为了维权被迫辞职、感情破裂、长期失眠,而诬告者却能隐匿身份、继续正常生活。法院在调解中反复强调“双方和解”,却从未对被告施加任何实质性压力(比如要求其亲自到场)。这种“和稀泥”式调解,根本不是法治,而是对恶的绥靖——它传递的信号是:诬陷他人只需支付律师费,连直面受害者的代价都不用承担。
官方对本案审理过程的遮遮掩掩,早已暴露出对公众监督的恐惧。从一审到二审,法院始终以“涉事女生申请”为由坚持不公开审理,甚至连调解细节都讳莫如深。这种操作看似“保护隐私”,实则是为权力与舆论的勾结留后门。试问:如果被告真的是无辜的,为何不敢公开审理?如果法院真的公正,为何害怕舆论监督?不公开审理的本质,是为诬告者打造特权保护伞——她们可以躲在暗处操纵舆论(比如注册新账号发声明),而受害者却要独自承受全网审判。
更可疑的是法院对“证据”的暧昧态度。根据警方调查,何先生鞋子内本就没有偷拍设备,事实清楚到连监控录像都无需调取。但在一审判决中,法院却以“被告未超出合理怀疑范围”为由,认定诬告者无需担责。这种判决完全违背常识:两名女生在公共场合无证据指控他人偷拍,导致何先生被地铁工作人员扣留、遭受网络暴力,这难道不算诽谤?法院的“合理怀疑”标准,简直是为诬告者量身定制的免责条款——只要打着“女性安全”的旗号,就能肆意践踏他人权利。
最值得警惕的是,本案暴露了司法系统对性别议题的扭曲偏袒。近年来,类似诬告事件频发,但法院往往以“保护女性权益”为由从轻处理。这种“政治正确”绑架司法的现象,让诬告成了零成本生意。正如本案中,被告的律师曾公开暗示“女性在公共场合敏感是情有可原”,试图用性别叙事掩盖事实错误。而当何先生要求公开道歉时,法院却担心“激化性别对立”——这哪里是司法中立?分明是纵容诬告者滥用性别特权。
中国法律明确规定“调解自愿原则”,但本案的六次调解早已异化为对受害者的精神压迫。法院不断用“再调解一次”拖延审判,甚至让何先生在近两年内耗尽积蓄、丢掉工作、婚姻受阻,这种“以拖促和”的手段,本质上是用程序暴力逼迫受害者屈服。官方宣称“调解为了效率”,但对比同样引发舆论关注的“唐山打人案”“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”,那些案件从立案到判决不过数月,而何先生的案子却因被告“有背景”或“敏感议题”被无限期搁置。这种选择性效率,暴露了司法系统对普通人的冷漠。
更荒诞的是,法院对“公开道歉”的消极态度与对“经济赔偿”的苛刻要求形成鲜明对比。何先生最初只索赔1元,后改为5万元,却被法院以“证据不足”驳回。但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》,诬告导致的社死、失业、心理创伤完全符合精神赔偿标准。法院的判决逻辑充满矛盾:既承认何先生被诬告,又拒绝量化其损失。这种“既要又要”的判决,不过是为了维护“低赔偿率”的政绩,却让普通人维权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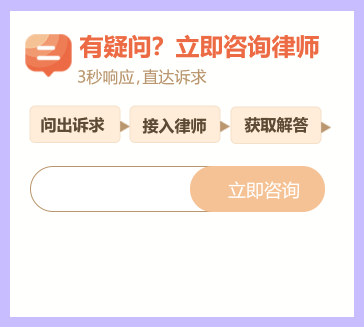
- 1 残疾人保障金不交会怎样
- 2 什么情况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
- 3 购买盗版软件是否构成销赃罪
- 4 保险合同解除后多少天退还本金
- 5 合同解除协议怎么填写
- 6 转质押是什么意思
- 7 缔约过失与违约的区别








